2009年,为了回应“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教育部联合中组部、财政部启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
它的目标是在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优势基础学科建设一批国家青年英才培养基地,改革拔尖人才教育的训练和培养模式,培养世界级的科学家。
今年是“拔尖计划”实施15周年。从1978年中国科技大学创建第一个“少年班”,到2020年“强基计划”的提出,我国探索改革高校学术英才培养已有46年。近两个月来,武汉大学“雷军班”、清华“巅班”和复旦“相辉学堂”等招生计划陆续引起热议,也让人们开始关注各个高校的“创新班”“尖子班”。
在“拔尖计划”提出的同年,清华大学启动“学堂人才培养计划”。它的核心理念是,将“学堂班”的学生定位为“领跑者”,让优秀的学生领跑,让所有的学生优秀。
当创新人才成为培养目标,面对更多拔尖的同学、更高难度的课程和更早开始的科研训练,这些进入“拔尖计划”的学生们,并非每个人都能找到方向保持领先。有学生成为“领跑者”,逐渐确立自己真正感兴趣的研究方向深入探索;有人慢慢地落在后面,成了默默无闻的普通优秀学生;也有人选择了退出。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这些班级的选拔和培养模式也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反复迭代。如何识别并选拔到最适合的具有创新潜质的人才,在以培养创新人才为目的的同时,关照每一个具体的人的需求,让所有学生发挥最大潜能,成了回答“钱学森之问”绕不开的问题。
“拔尖”
“为什么选姚班?因为姚班最难进。很多人都会选分最高的专业,不然觉得白考了那么高分。大部分人其实不知道自己应该选什么。”在进入清华前,刘皓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学计算机。
刘皓曾经的梦想是做一名天体物理学家。中学起,刘皓开始参加全国中学生物理竞赛。他形容自己就像真正的奥林匹克运动员一样训练,每天至少花4个小时刷题,在假期里翻一番。
后来,刘皓成为省里历届比赛第一个取得一等奖的高一学生,并在高三取得金牌,保送清华大学。刘皓咨询当时还不招收本科生的清华天文系老师,对方告诉他如果想当天文学家,不仅物理基础重要,计算机基础也同样重要。在老师的建议下,他选择签约进入“姚班”。
在计算机系甚至整个清华,都流传着“姚班”的神话。2004年,图灵奖首位华人获得者姚期智辞去在美国普林斯顿的终身教职,回国到清华大学任教。他想创立一个世界上最出色的本科班之一,缩短中国计算机领域和世界领先水平的差距。第二年,“姚班”正式成立,并被率先纳入清华“学堂计划”,全称为“清华学堂计算机科学实验班”,旨在培养领跑国际拔尖创新计算机科学人才。
“姚班”的神话吸引着一批最优秀的学生慕名而来。许楠在初中参加信息学竞赛时就听说过,“姚班”的录取名单上几乎全是保送进去的数学和物理奥林匹克竞赛国家集训队选手,还有少数的各省高考状元。他抱着“见见世面”的心态报考了“姚班”的二次招生。
那次,许楠参加了一场两个半小时的数学物理联考。当接到被“姚班”录取的通知时,许楠的第一反应是“冒充的诈骗电话”。后来他得知,与他同届的90多名学生中,只有少数学生通过二次招生进入。
在成为省高考状元的那一年,张涵选择进入清华另一个拔尖人才的聚集地——“钱学森力学班”。那里同样汇聚了众多竞赛得奖者和高考状元,少数学生通过二次招生进入,每年只录取30人左右。
“钱班”还是“拔尖计划”唯一定位于工科基础的试验班,由郑泉水院士担任首席教授。2007年,郑泉水向清华大学校领导提出,结合清华的力学和工科优势,创办一个“人才培养试验田”,并获得了当时在病榻上的钱学森院士的许可,以他的名字命名这个班级。
张涵选择“钱班”的理由是,“它不限制你的发展方向”:这里以工科为基础,但没有明确的专业方向,针对学生进行多学科前沿交叉创新培养。
“以科研为导向”也是“拔尖计划”班级的最大特色之一。刚刚进入“钱班”时,张涵发现,“如果不提前预习,连跟上老师的节奏都有些吃力”。但这些课程也的确与众不同:“老师不是在教你解题方法,而是背后的本质和理论来源”,张涵说。
同样,当优中选优的“尖子生”进入“姚班”后,也面对的是以培养创新人才为目标而准备的前沿课程。首席教授姚期智带领团队为学生制定了“深耕精耕”的培养方案,融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普林斯顿大学等世界一流高校的计算机教育先进方法,核心专业课程采取全英文授课。
在刘皓看来,培养科学家是“姚班”的最终目标,这里强调培养学生做研究的能力。曾担任过普通物理和量子信息方向课程助教的一名博士生认为,“姚班”的本科生专业课程比研究生课程更为深入,目的是使学生了解这个领域的前沿,并能够流畅地阅读这些文献。老师会向学生展示最近一两年才发现的新现象,和至今未被解决的难题,激发学生思考。
许楠几乎不缺勤任何一节课,“如果我不去听课,我就真听不懂了”。他认为,这些入门课程一点都不“基础”,“姚班”的专业课进程飞快,一个学期里教授的内容远超计算机系的课程内容。
大池塘里的小鱼
尽管刘皓是通过保送进入“姚班”的大多数,但他发现自己对计算机学科几乎没有任何概念,有时甚至听不懂同学的谈话。远离了天文学家这个目标的指引,刘皓第一次感到如此迷茫。
然而,刘皓并没有在十字路口停留太久,尝试科研成为了他走出迷茫的一条路。“姚班”一直以来都有着鼓励学生走向科研的土壤。他开始联系教授,进课题组做科研。
刘皓曾在上课时获得研究灵感,密码学基础课的老师鼓励他们用机器学习破解一个密码学的难题。起初,刘皓只是把它当作一个课程作业进行尝试,后来越做越感兴趣,科研成为“主业”,上课变成“副业”,最后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成功解决了一部分问题。
在同样强调研究学习的“钱班”,张涵也很快找到方向。参加冬令营时,她记得在实验室用一把激光枪打到石头上,再采集受到灼烧的材料,分析它的元素和含量。这让她觉得科研很“酷”,是“动手创造的过程”,还能够发挥很多实际价值。
张涵走上科研道路,对她来说更像是水到渠成。从大一到大四的每一步,以科研为导向培养人才的“钱班”都有具体的课程训练,让学生们在研究中学习。从最初在大项目中“打工”,到自主提出研究问题,张涵逐渐积累科研素养,也意识到,自己真正喜欢做实验。
然而,相比于这些早早就能快速适应、明确学术方向并找到研究兴趣的学生而言,并非每个人都能在同样的培养模式下被激发出内生动力并甘之如饴。在“钱班”,李嫣做科研更像是“早开始晚开始都得开始”的随波逐流。她在大一进入课题组做理论推导和仿真实验。但真正开始后,她发现自己不仅不会做仿真实验,就连相关文献也很难读懂,需要“现学”理论。
当一群拔尖人才聚集到一起,差距也随之显现。作为少数通过二次招生进入“钱班”的李嫣,在只有30个人左右的小班课堂上,依然觉得“能被看到的永远是在前面的少数,后面的大多数是看不到的”。
李嫣时常感到挫败。平时听完专业课后,她还要自学,有时从早到晚只能做完一个作业,周末时间也几乎全部用来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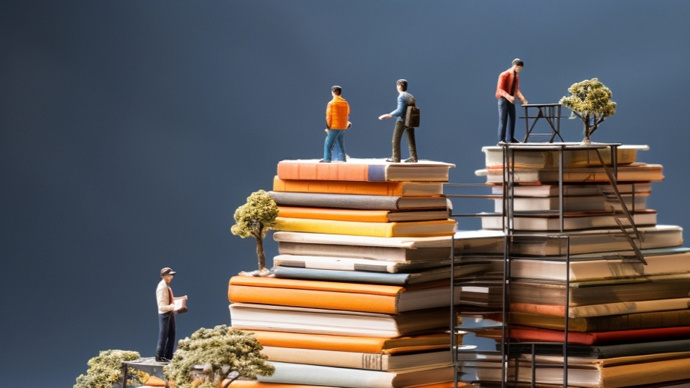
 相关论坛
相关论坛
 热门广告
热门广告
